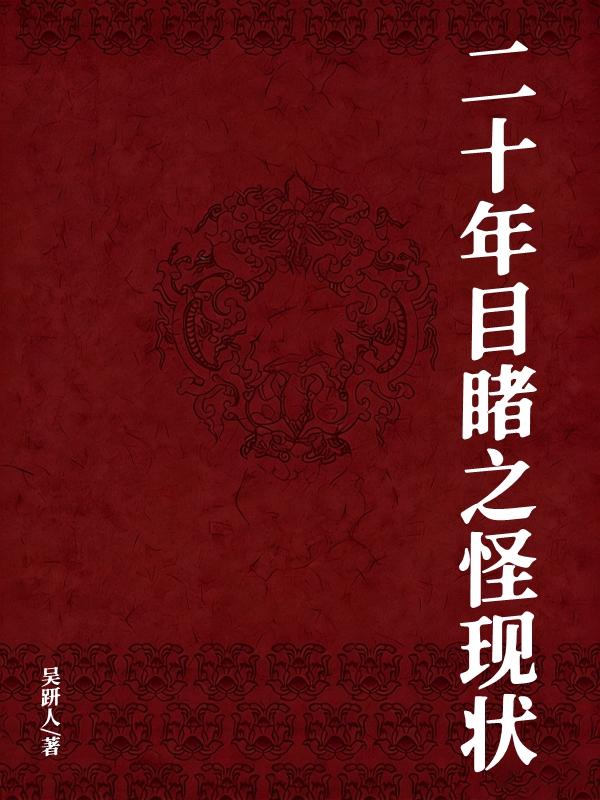第二章 天牢
那个人被放了下来。我也没看清楚人家是怎么将他解下来的,好像一挥手,那人就如同一袋子土豆似的掉到了地上,看来是有机关的,只有我那么笨,还用刀子割绳子。
两个人上来,一边一个架起他的胳膊将他拖走了。他的头垂着,只能看见乱蓬蓬的头发,地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,看得我心肝儿直颤。不管他犯了什么罪,都不该受这样的折磨。
还没等我进一步悲天悯人,就有人上来将我解了下来。一件灰头土脸的衣服和一双破布鞋“啪”地扔在我脚下。那人上下打量我,呵斥道:“快穿上!”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,黑色的吊带裙已经被鞭子打破了几处,露出几道青紫色的鞭痕,再看看胸前也咧开了,连内衣都露了出来。我脸一红,赶紧拿起地上的衣服,手忙脚乱地套在身上,衣服很长,拖到了地面。我偷窥了那几个人一眼,见他们表情只有不耐烦,不见淫亵,放下心来。都是公公啊!这个发现让我很是欣慰,虽然是变态,总比一群如狼似虎的雄性动物安全。
那几个人推着我的肩膀让我往前走,我又经过了那道石壁走廊。此刻,两边的石壁上都点燃了风灯,昏暗的光线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如鬼影一般。
来到走廊的尽头,右手边隐隐可见一排排的牢房,呻吟哀嚎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,仿佛地狱的魔音,让人不寒而栗。
幸好,我被推着转到了左边,与刚才是一样的石壁走廊,却越走越安静,渐渐听不见其他的声音,只闻我们的脚步声,因为寂静,因为未知,越发让人从心底渗出恐怖来。
走廊的尽头灯火通明,在一面墙宽的铁栅栏后面只有一间牢房。押着我的那几个人打开门,在我背上狠推了一把。我直接以“平沙落雁式”扑在地上。
伸手摸摸,脸还是立体的,没给拍成照片。爬起来,四处张望,我一路已经做好准备了,会被关入一间阴暗潮湿,散发恶臭的牢房,地上跟动物园一样跑着蟑螂和老鼠。没想到这里很宽敞,还异常的干爽整洁。最重要的是只有这一间牢房,根本没有其他犯人,可见这个半死的人是个要犯,才会单独关押。我很感慨,天牢里也有VIP总统套啊!
牢房一面是铁栅栏,三面是石壁,在高墙的顶上,有一个两张A4纸那么大的窗子,还镶着铁条。地上有些稻草,靠墙的一面是个石台,像张床,上面也铺着稻草,四个角上立着四根铁柱子,应该是绑人用的。此刻刚才被打得体无完肤的那个人趴伏在上面,手上脚上还带着粗粗的镣铐。
我突然顿住,回过味儿来,转身发疯一样拍打着已经锁上的铁栅栏门,“放我出去,给我换一间单人的。”
门外要走的几个人停住,回头呵斥:“单独关押的都是死囚,你还担不起那个罪名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哦!那我就不住单间了。
我可怜巴巴地尝试着说服他们,“那将我关到女囚那边可以吗?”
那人很是铁面无私,丝毫没有一丝的怜香惜玉“马公公吩咐了,让你照料这个人,别让他死了。他该受的苦刑还没有受尽,若他死了,就都加在你身上!”
我心中波涛汹涌,无比悲愤。太不人性化了,竟然将我跟一个半死不活的男犯人关在一间牢房里。还有天理吗?一个好的监狱应该是人性化的管理,是犯人洗心革面,重新做人的地方,是失足的人,人生新的起点……
算了,长耳朵的都走光了,剩下这个比我还倒霉,我就不抱怨什么了。我又渴又饿,如不是这该死的穿越,此刻我应该是骗完吃喝,功德圆满地躺在宿舍的床上了。
我只好回身又打量了一下牢房,屋角处有个水缸,还有一个金属盆,栅栏和床之间有一个黑不溜秋的桶,马桶呗,不用细看我也知道,动动鼻子就行了!
我看了看石台上趴着的人,连是否有起伏的呼吸也看不出来。我大着胆子走过去,试着推了推他,小声道:“喂,你可别死啊!”
其实这会儿,我倒没去想他死了,我得替他。我只是害怕他死在牢里,我得跟个死人呆一晚上。那可太恐怖了!
此刻我看着这个人,他的生死不明,比目前自身的处境更让我害怕。我伸手探到他的鼻下,感到微弱的气息,如小鸟的羽毛,一凉一热地吹着我的手指,心中竟然涌起对他的感激。他还活着,太好了!
?
铁栏外有人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,不是刚才的那些人,而是个六十开外的老狱卒,有点儿颤颤巍巍的,来到铁栏前,将些饭菜、一小罐水连同一件衣服顺着铁栏的缝隙递进来。见四下无人,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罐子放到栏内的地上。他向着石台上趴着的人张望了一下,随即叹息了一声,“唉,好人没好报啊!”说着,摇头走了。
牢房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。我走过去,先拿起那个罐子,打开一看,是膏状物,闻了闻,有股草药味儿。我又从角落的水缸里打了盆水,就着灯火看了看,还挺清澈的。我将水盆和药膏都放在石台上,想了想,从自己衣服的下摆撕了条布下来,浸在水里,淘洗一下拧干了。
他身上的衣服已经是一条一条的,没什么阻挡,我轻轻地除掉他身上的碎布,擦拭他血肉模糊的后背,这才看到,他的背上有鞭伤,也有烫烙过后,露着红肉,淌着黄水儿的烫伤……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我是个胆小的人,中学的生物解剖课向来都是捂着眼睛过来的,更别提躺在我面前的是活生生的人!我颤颤巍巍地为他擦掉血污,又在他的伤口上抹上药膏,也分不清伤口不伤口了,反正他已经没有一块好肉,我整个涂抹就行了。然后是他的腰臀和腿。
背面完事了,我将那盆血水泼到铁栏外面的地上,又换了盆干净水回来。把他翻过来让我犯了愁,别看他瘦的皮包骨头,可是还真沉啊!我又不敢玩命儿推他,只能尝试着将手插到他腋窝下去提他。我费了吃奶的劲儿,也没把他翻过来,一屁股坐在地上倚着石台喘粗气。
过了好半天,我正蓄精养锐,准备再接再厉呢,就听背后有一阵铁链的唏哩哗啦的声音。我回头,看见那人正费力地自己转过身来。我赶忙跳起来去扶他。在我的帮助下,他终于仰卧在石台上,浑身抖做一团,半天才忍过去。
我等他不抖了,就接着为他擦洗,他的前胸和腹部比后背还惨,看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咬咬牙,拿起手里的布尽量轻地为他擦,可是碰到他时,还是让他畏缩着蜷起来。压抑的呻吟溢出他的唇角,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出声。他极力控制着自己,慢慢将蜷成虾子一样的身体打开。
我细心地擦净他的身体,仅是前胸和腹部就让我换了两盆水,又为他涂上药膏。接下来,再往下……我有些踌躇,毕竟是个男人!他衣不蔽体的,看得出下面也有鞭伤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,他闭着眼睛,一动不动。好!讳疾忌医是要不得的。我为自己鼓鼓劲儿,直接把手里的湿布按在他下面,没敢细看,面红耳赤地涂上药膏,顺手将那件干净衣服拽过来,搭在他腰间,才呼出一口来。还好他没什么反映,了无生气地躺着,也不知是不是又晕过去了。
接下来容易些,他的胳膊、腿和脸,我也一一擦过,又涂了药膏。他的脸肿得跟猪头一样,即便擦掉血污还是看不出长相年纪。他的手腕和脚腕有些难处理,被铁镣磨得都露出惨白的骨头。我只能又从我身上衣服的下摆和袖子上撕下布来,一下子袍子变成连衣裙了。将布叠好,小心地缠在他手腕、脚腕的镣铐上,虽然作用不大,但是好歹垫一垫吧!
都好了,我将那件干净衣服套在他身上,还好是件开衫,袖子部分就从镣铐的缝隙间塞过去。我出了一身汗,才将衣服给他穿上,又将带子系好。他终于有点儿人模样了。
我走过去,从地上拿起水罐,虽然我口干舌燥,嗓子都冒烟了,但还是倒出一碗水拿到他嘴边,他就着我的手,喝了几口,便极轻地摇摇头,表示不要了。
原来他醒着呢!反正他眼睛肿得只剩下一道缝,我都看不出他是否睁着眼。想想刚才,我脸有点儿发烧,故作镇静地说:“你失血过多,应该多喝点儿水。”
他很听话,果真将剩下的半碗都喝了,又躺那儿装死。
我抓起水罐,仰头直接将水倒进嘴里,喝了多半罐,才感觉好些!
我看了看饭菜,倒是一荤一素两个菜,还有碟馒头,一碗粥。看来牢里伙食还不错,也不知道是特殊优待还是大伙儿都吃这个。
看他那样子,馒头和菜肯定是咽不下去了,待会儿还是便宜我自己吧!于是我端起那碗粥,小丫鬟上身地舀起一勺凑到他嘴边。他虚弱地摇摇头。我轻声劝他,“好歹吃几口,你若死了,我可没有你这么能熬。”
自己也觉得很无耻,竟然如此威胁一个只剩下半条命的人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,也许是因为刚才老狱卒的话,也许是因为他受尽折磨依旧如此坚强,反正,我直觉地感到他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。
果真,他张开嘴,含住我手里的勺子。吞咽的动作带给他很大的痛苦,他呻吟着,手扒着石台的边缘,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那一小勺粥咽下去。
我都不忍心了,他却又微微张了嘴……那一碗粥,足足喂了半个小时。别说他了,我都浑身直哆嗦。
我用湿布揩掉他额头的冷汗,“你睡吧,我守着你。”
事实是,我狼吞虎咽一通,又胡乱洗了一把脸,躺在地上的稻草堆上就睡着了。
?
当第一缕阳光照到我脸上时,我腾地一下子坐起来,嘴里叨咕着,“坏了坏了,今天要论文答辩的!”
我跳起来,惯性地去抓床栏上搭的衣服,才发现伸手抓了一把稻草。对着手里的稻草发了一会儿呆,一时悲从中来,原来不是做梦啊!
来不及为自己的处境伤心,我一骨碌爬起来去看石台上的人,见他胸膛一起一伏地,还喘气呢!只是睡得极不安稳,蹙着眉头,不时发出呻吟声,声音不大,可是异常让人揪心。
在我的注视下,他好像醒了,我也不能确定,因为他睁眼还是闭眼,我也看不清楚。只是他停止了呻吟,静静的躺在那里,连胸膛的起伏都小了,仿佛凝神屏气一般。
我很无聊地问了一句,“喂,你醒了吗?”
过了一会儿,他缓缓地点点头,硬撑着支起上身,大口大口喘息着。我弄懂他的意图,赶紧扶了他一把,让他坐起来。他挪到石台里边,将后背靠在石壁上,垂着头。
有一个年轻的狱卒过来,是昨晚押我过来的公公里的其中一个。将早饭和水顺着铁栏放在牢房里面的地上,还颇为恭敬地说了句,“请用早膳。”弄得我很是奇怪,对犯人这么客气?那还将这个人打得死去活来?
那公公直起身打量着我们,向着我点头道:“疯婆子,照顾得还不错,他都能坐起来了,给他吃些粥饭,一会儿马公公来了还要提审他呢!”
“还要打他?”我难以置信地冲口而出。
“这可是皇上的旨意,让锦公公督办。锦公公吩咐了,让他受尽慎行司的大刑。”我觉得他提到锦公公时比提到皇上还要毕恭毕敬。
狱卒转身走了,我看着眼前垂头而坐的人,一阵伤心。他依旧一动不动,如老僧入定一般,仿佛周遭的事物都与他没有关系。
我挣扎了一下,还是拿过水和一碗粥,他很顺从地艰难咽下,每吃一口都跟受刑一般。
不一会儿,几个人过来果真将他带走了,他们驾着他,拖着往外走,“嘭”地锁上牢门,我双手抓着铁栏,看着他们走远,心中惊惧惶恐。
隔了十几分钟,我好像听到人的惨叫声,并不真切,若有若无,仿佛只是我的臆想一般。仔细去听,又没有了。天哪!不会是我都幻听了吧!我伸手堵住耳朵,可是那声音还是丝丝缕缕地传了过来,我倚靠着铁栏,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……
我已经没有时间观念,只是觉得过了很长的时间,他又被人拖了回来,那些人将他仍在石台上就转身出去了。
马公公跟了过来,站在铁栏外面,拿着一块锦帕轻沾着额头的汗,“今天就到这儿吧,宫里还有事儿呢!咱家先回去了。”
说着,以锦帕扇风,转身走了,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看了我一眼,“呦,洗干净了这小模样还真是受看。丫头,下次再来劫狱,在脸上戴块黑布不就行了吗?用得着抹灰吗?”
见他如此求知好学,不耻下问,我本着互通有无,沟通研讨的精神呐呐着说:“这个……戴黑布影响呼吸顺畅,况且还容易脱落,往脸上抹灰简单易行,遮掩效果也更好。与敌人一打照面,还能起到震慑作用。对方以为见了鬼了,一呆之下,我方就能取得先机。”
马公公扇着手帕,转着眼珠想了想,兰花指一指跟过来的监牢文书,“有理,记下来。”
那文书哆嗦了一下,差不多是幽怨地看了我一眼。
等他们都走了,我扑过去看石台上的人。到他跟前又放缓了脚步,不忍看啊!他自己已经面向墙侧卧过去,缩成一团。
我蹭到他跟前,见他身上倒并无大碍,衣衫还是完好的,没见多了鞭痕血迹,微微放心。只是他蜷曲着,我看不到他正面。
我伸手轻拨他的肩膀,他浑身哆嗦了一下,没动。我微微用了力,将他翻过来,粗粗打量一下,也还好,只是面色惨白,头发都被冷汗濡湿了,贴在青肿难辨的面颊上。我顺着他的脸往下一看,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,他的手……
他的手指青紫,指尖满是血污,指甲翘了起来,指缝间是血窟窿,还在汩汩地冒着鲜血。十指连心,该有多疼啊!这群死太监,变着法儿地折磨他。
心下咒骂着,手里却没闲着,打过一盆清水,沾湿昨天的布为他擦洗。又为他的手涂上药膏。想了想,从身上的衣服下摆又撕下一截儿布来,得,这回长裙索性变短裙了。将布缠在他手上,才将他的手轻轻地放回胸前。他一声不响地躺着,不知是不是睡着了。
?
我给他喝了几口水。又有一狱卒过来,将中饭摆在地上。看他那样子是吃不下去了。我的肚子倒有点儿饿,可是比饥饿更难耐的是另一方面的需求,难以启齿啊!想我穿过来都快一天了,我这……人有三急,皇上老子也要上厕所呀!
我尽量不去想,我忍!可是那种感觉却不受意志的控制越来越强烈。我开始后悔,刚才没人的时候我怎么没想起来呢?光顾得担心害怕了,竟然没有抓紧时间解决这个个人的问题,郁闷啊!可是一想到我还在这儿指不定要呆多少天,更是让我欲哭无泪,都快忍不住了。难受得我,捂着肚子围着马桶转了三圈,可是牢里躺个男人,外面不时还人来人往的,作为二十一世纪受过教育的文明人,我还真是拉不下这个脸。心里咒骂着,果真太监都是心里变态,竟然将我跟一个男人关在一起,太羞辱人了!
在我绕第六圈的时候,石台上传来唏哩哗啦的动静。我回头一看,那个人费力地支撑起自己的身子,将两条腿搭在地上,垂头忍耐了一会儿,等到痛意稍缓,便颤颤巍巍地扶着石台站了起来。我呆看着他,不知他要干什么。只见他双手扒着石台的边缘,艰难地挪着步子,好像随时会跌倒,走一步,就停下来喘息一会儿,再走一步。短短几步却费了几分钟的时间,才来到铁栏前。他背靠着铁栏缓缓滑坐在地上,将头扎在腿间,抖了一会儿,举起一只手,以腕上的铁铐敲击铁栏,在空旷的牢房里发出“哐、哐”的钝响。
很快,有狱卒过来,神色颇为不耐烦。
地上的那人依旧垂着头,“给我床被子。”他声音很小,沙哑难辨,如漏了洞的风箱,有些“嘶嘶啦啦”的。而且不像是祈求,更像是命令。这是我一天来,第一次听他开口讲话,原来不是个哑巴!
随即,我为他担心起来,作为一名要犯,还如此张狂,不知收敛,还敢要被子?正在我以为他又要招来一顿辱骂毒打时,那个狱卒犹豫了一下,却恭恭敬敬地答道:“是。”须臾,还真拿来一床破旧的薄被。让我不禁对这个垂死的人刮目相看。这就是人的气势啊!
那人拿起扔在地上的被子,并没有盖在身上,而是揪着铁栏费力地从地上又爬了起来,冲着石台与铁栏中间的马桶挪去。我以为他要上厕所,本想扭过头去,不过他那个跌跌撞撞的样子实在令人揪心,就跟在他后面很八卦地问:“你用?你先用,要不要我扶你?”说完自己也觉得脸红,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。
来到马桶边,他用缠着破布的手指,将被子的一角系在铁栏上,挪了两步,将另一角系在了石台一角的铁柱上。这才一下子跌坐到地上。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马桶前长出个门帘来,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那人半坐在地上,向牢房的里角挪去,应该说“爬”,更确切些。然后蜷缩着面向墙壁躺在了离马桶最远的墙角里。
我此时才反应过来,跑过去看他,见他一动不动,好像昏死过去一样。眼中一热,差点落下泪来……
从那以后,这个人基本上就缩在那个角落里了,我让他睡到“床”上去,他跟没听见一样。我试着去抱他,他轻轻推开我的手,哑声说了一句,“地上凉,不那么疼。”
我也明白他是想将那个“床”让给我,很是感动,这个人受尽磨难,却还惦记着别人,就冲这一点,我也认定他不是个坏人。不忍再拂了他的好意,只能在他待着的角落里铺些稻草。
晚上,是那个送药的老狱卒值班,我向那个老狱卒要了一床被子,和一件干净的囚衣,重新为他擦洗了伤口,抹了药,又将他的手指换了干净的布包好,这才将被子盖在他身上。
老狱卒叹息道:“姑娘,你是个好心人呐!”
我见那人似乎是睡着了,不禁走到铁栏前轻声问那老狱卒,“他犯了什么罪?要这么对他?”
我真的是很疑惑,通过两天的观察,我觉得那些人并不是为了从这人嘴里得到什么秘密而严刑逼供,根本就是为了折磨他而折磨他。他身上的伤口虽然骇人,但没有一处是致命的,可以说那些人很小心,甚至腹部的一道很深的伤口也被针线缝上了。给我的感觉是,他们不想杀他,也不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,就是想让他死不了活受罪。
老狱卒警觉地四下看了看,凑到铁栏前,小声道:“哪有什么罪,不过是不肯低头罢了。”他进一步压低了声音,“他得罪了当朝的首辅高大人,皇上也是忍痛降旨关押他,不想落在锦公公手里,可受了大罪了!”
我听得一头雾水,不过却有一个模糊的轮廓,听上去,那个首辅高大人和锦公公都比皇上硬气多了,可是这个人竟然得罪了两个比皇上还要厉害的人。
老狱卒又狐疑地看向我,“这事儿朝野内外没有不知道的,姑娘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啊!”
我赶紧说:“我是异乡来的,刚到这儿莫名其妙的就被送到牢里来了,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,他是谁啊!”要说好奇害死猫!女人的通病。
老狱卒半信半疑,随即摆摆手,“你要是不知道,也不用打听了,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去,哪天锦公公一高兴要了他的命也说不定的。造孽啊!”说着转身蹒跚而去。
夜深了,牢里的灯火大半都熄灭了,我转身在昏黄的光线下看向那个人,在角落里蜷成一个淡黑色的剪影,凄苦却依旧不容践踏,让人心生敬意。
第二天一早,马公公就来了。他也没个节假日休息,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,放在现代,早就是劳模了。
他隔着铁栏对着角落里的人张望,“气色还不错,昨儿您歇够了吧,那今天就给您松松筋骨。”
接着吩咐左右随行的人打开牢门,以手叉腰,在一边训诫道:“锦公公他老人家说了,忙完这几天的事儿就过来看他,你们大伙可精心着点儿。”
眼见他们架起他就往外走,情急之下,我不禁脱口而出,“等等!”
马公公回头看我,“丫头,你又怎么了?”
啊?!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但我的本事就是绝对不会冷场。
“马公公,其实你们已经很尽心竭力,尽忠职守了,就这么一个人,众位大人能够如此不辞辛苦,不分昼夜地刑讯,实在让我钦佩。人们常说,难的不是做一件事,而是不停地做同样的事儿。这么天天打他,你们都能不腻烦,都能保持如此昂扬的战斗力,都能推陈出新,孜孜不倦。这不仅仅是忠心耿耿,不仅仅是敬业爱岗,不仅仅是……”
照我的实力,我也就是刚说个开场白,第一轮的车轱辘话还没开始呢,马公公就脸皱得跟苦瓜一样打断我,“小姑奶奶,你能捡要紧的说吗?”
我顿了一下,最初的紧张消失后,我的头脑稍稍清晰了一些,言语也可以先到大脑,再到嘴里了。我小心地审词度句,想了想开口道:“马公公,锦公公是不是对此人恨之入骨?”
“这个吗?我爹锦公公他老人家的心思谁能猜透呢?只是他特意吩咐下来,将慎行司的大刑尽数用在此人身上。”
好家伙,这还不是一般的不共戴天呐!也不知道是杀父之仇还是夺妻之恨呢?
“听闻锦公公过几天要来牢里看他,要是到时候他半死不活的,岂不是坏了锦公公的兴致?”我大着胆子说出来,自觉一副狗腿上身,助纣为虐的小人嘴脸。
马公公扭着身子,把自己站成了一根麻花,一手还托着腮帮子,“丫头,此话差异。这是锦公公吩咐下来的,这个人越是惨不忍睹,他老人家越会高兴才对呀!对了,咱家想起来了,”马公公一拍手,“昨天晚上,咱家躺在床上睡不着觉,忽然想起来一个有趣的办法,若是将此人倒吊着,四周燃上炭火,再用铁刷子……”
“马公公,马公公,”我赶紧拦下他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,这也是个发明创造型人才啊!“马公公的想法真是令人钦佩,只是不知道锦公公是否能了解您的一片苦心?其实,若能让锦公公亲眼看见您费心费力,他老人家才会对您刮目相看。”
马公公转了转眼珠,“丫头,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我的意思是不如让这人休养几天,养好了,等锦公公前来亲自观刑。若是到时候这个人已经气息奄奄了,那还有什么行刑的意义?您的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妙想也无法得以施展。”
马公公频频点头,“有点儿意思。”
见他有所松动,我赶紧乘胜追击,晓之以理动之以情,“说不定锦公公还要亲自动手呢!您想想,折磨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有什么意思?亲手将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折磨到求生不能,求死不得方能让锦公公得以消除心头之恨!”
马公公翻着眼睛想了半天,下定决心道:“好,丫头,咱家就听你一回。若是我爹他老人家满意,自是皆大欢喜;若是他老人怪罪下来,咱家可是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可明白?”
“明白,明白。”我小鸡啄米一样点头。
那伙人果真将那人扔了回来。我看着他趴伏在牢房里的地上,吁出一口气来,这才发现额角的头发都被虚汗浸湿了。
至少,他可以过两天太平日子。我能做到的,也只能是这么一点儿了。
狱卒送来早饭,不过是稀饭和几个馒头。我心下恻然,连递给他食物的勇气都没有。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?我为他疗伤,给他吃东西又是为了什么呢?就是为了让他养精蓄锐,好接受更加残暴的摧残吗?
他却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,来到盛放早饭的托盘前,拿了一个馒头,退回到角落里,将馒头掰成小块儿,安静地送到嘴里……
?